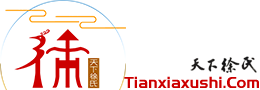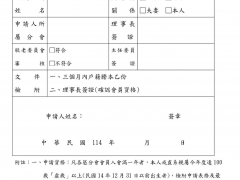中国虽然是发明活字印刷的国度,并且按照元朝人王桢在《农书》中的记载,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出现锡制金属活字,但在引入西洋印刷技术之前,整版的雕版印刷,一直在书籍出版印刷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相形之下,活字印书始终只是一种很次要的陪衬,金属活字印本,更是微不足道。所以,传世活字本要大大少于刻本,其中铜活字等金属活字本,又大大少于木活字印本。收藏的基本原则,是以稀为贵,活字本、特别是金属活字印本,其价格明显高于刻本,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丝毫不足为怪。
关于活字印刷在中国未能兴盛的缘由,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解释,但似乎还不够十分清晰,有待进一步分析总结。不过,与此相比,当前更重要、同时也更为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应该是重新审核中国古代采用铜等金属活字印书的真实状况。因为时下被普遍认作铜活字印本的许多中国古籍,特别是其中的所谓明铜活字印本,其实并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恐怕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更不用说一些印刷史研究者所持早在宋代中国即已有铜活字印书的主张,恐怕纯属想当然的说法,浑然不知其究竟是从何说起。
从学术上一一论证这些问题,需要花费很多笔墨,不适宜在这里讨论,我将另行发布论文,与关注版刻史和印刷史的朋友讨论。不过,有一项原则,必须声明,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宗旨,是揭示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及其内在本质,求真是它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学术问题,不能带有过多的个人感情好尚,更不宜怀有本民族或者是本国自身的文化必定要事事优越于人的狭隘情结。就书籍出版印刷而言,我认为古代朝鲜的铜活字印刷,不管在行用时间的早晚上,印刷技术的发达完善程度上,还是印书的份额、数量和施行的普遍性上,都要大大领先于中国,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假若由此再进一步探究,中国铜活字印刷的产生,实际上很可能是直接受到西洋以及朝鲜印刷术影响所致。这样的迹象,已经相当清晰,我将另行撰文,加以说明。
世界各国的文化,都是在交互影响中发展。印刷术虽然是由吾国先人所发明创造,但在其问世之初,就带有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其捺印佛像这一技术源头,就清清楚楚地是由印度传来;晚近西洋活字法印刷技术彻底改变了中国印刷的面貌,更是世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漫长的发展期间内,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若是在某些方面,受到周边地区甚至泰西工艺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必每一项技术环节都一定非由中国向外辐射不可。况且积极吸收外来文明以壮大自身,本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人类文明的成长,不同于豢养赛狗赛马,“纯种”的文明,往往意味着弱智、痴呆乃至消亡,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好事。假若不能忠实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冷静地分析各种史料,恐怕很难得出足以服人的结论。
辨认铜活字等金属活字印书,目前应该已经具备一定技术手段,这就是通过显微放大印本的墨迹,似乎应不难辨识金属活字与木活字印痕的差别,据闻已经有人做过成功的实验,并出版了专门的著述。至于能否通过检测印本墨痕中残留的金属微粒,区分出所用活字属于哪一种金属,似乎还有待验证。不过,若谓不经技术手段检验,或是依赖其他间接的辅助办法,就单凭肉眼观察来区分印本所用活字的种类,哪怕只是简单区分开金属活字与木活字(或是泥等其它材质的活字),除非怀有特异功能者之外,平常人恐怕很难做到(如张秀民、黄永年等先生就都坦然承认这一点)。所以,以往认定的铜活字印本,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书中的注记题识,或是相关的文献记载。如果这些文字记述统统明确无疑,譬如像清内府用铜活字印行《古今图书集成》,这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假若相关的标识记载含含混混,不甚清楚,譬如像所谓明铜活字本那样,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就需要综合分析各种相关史事来作出合理的判断,万万不可像藏书家估价自己藏书的价值那样,抱有尽量往多里算、尽量往好里算的念头。
在活字印本特别是铜等金属活字的实际鉴别活动当中,由于印本流传稀少,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既有相应的研究能力和探究兴趣,又有较多机会,得以直接目验其书,参与辨识;其它大多数关注印刷出版史事的人,往往只能被动地遵从他们的结论。若是用一犬吠影、众犬吠声这句成语来比喻此中情形,虽然不甚适宜,且多少有些失礼,却也算得上是差相仿佛了。其实,这本是在许多研究中所共有的现象,并不是只存在于版本鉴别领域。不过,麻烦就麻烦在鉴别版本时的这个“影子”,往往不易看清究竟是人影、贼影,还是鬼影,有时甚至根本就完全是没有“影子”的“幻影”,由于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个偶然失误,不经意间,被人错认,致使后来者相继将错就错,终至弄假成“真”。在我看来,在中国的版本学界和印刷史研究领域当中通行的所谓清铜活字印本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就是这样一部书籍。
毘陵是常州历史上的古郡名,用古地名作为居邑的雅称,久已有之,但自明代中期以来,尤为普遍。这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便是常州徐氏家族在清咸丰年间纂修并印行的族谱。清代在常州以及江浙地区其它一些地方,纂修族谱的风气颇为盛行,有条件的家族,大致平均每隔三十年上下时间,就要重修一次,以赓续前脉,称此家谱为“九修”,就是为与此毘陵徐氏历次所修其它族谱相区别。
这种族谱过去不受文人重视,藏书家对它更没有兴致,晚近以来,受西方学术影响,才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受到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青睐,但与其所纂修的庞大数量相比,国内外学术机构的收藏,仍显得很不完备,并且一直缺乏综合各处收藏比较全面的联合目录(这主要是因为颇有一些集中收藏族谱的地方,还从来没有全面做过著录),再加上还有大量族谱,一直散存于民间,甚至还无法踪迹其存佚状况。所以,这部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究竟有多少传本存世及其藏身何处,现在都还不太清楚。当前,活字印刷研究者所依据的本子,是收藏在日本东京东洋文库的一部印本。虽然现在还没有人提出这部族谱另有传本藏弆,但某些人径称此东洋文库藏本为传世孤本,却似乎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中国最早将这部《毘陵徐氏宗谱》用作清代铜活字本代表的学者,是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张秀民先生(说见所撰《清代的铜活字》一文,原刊《文物》1962年第1期,后收入1988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页250~259);后来中国国内谈及同一问题的著述,直至今天,无一例外,都应当是在转述张氏的说法。张秀民先生对中国印刷史做过很多重要研究,当初筚路蓝缕,自然功不可没。不过,学术研究,后来居上,也是事之常理。时至今日,市面上刊布的很多相关书籍和文章,仍在一一依样复述张氏多年以前的所有说法,未能对其稍有订正补益,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诧异,同时也很遗憾。个别学者如江苏的潘天桢先生,虽然提出过很好也很重要的新见解,但却根本不被撰述通述性著述的学者特别是那些研究印刷史和版本史的名家所理睬。
面对西洋文化的巨大冲击,张秀民先生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颇有一些人热衷于到中国历史中去挖掘找寻与西洋近代文化相通相似的事例,以这些西洋舶来品在我国古已有之而自我慰藉。古代的铜活字印刷,在技术上显然与西洋晚近活字印刷最为接近。不知张秀民先生是不是因怀有上述对西方文化的趋从与自我印证心态所致,在鉴识古代的铜活字本时,确是颇有多多益善的味道,以致将一些缺乏足够证据而本可存疑待考的活字印本,率尔认定为铜字所印。类似的情况,在赵万里先生等人身上同样存在,从而足以说明,这恐怕不仅仅是张氏个人研究的局限所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那一时代在研究观念上的偏差所造成的结果。时至今日,我们对此不能不深深引以为戒。
当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秀民先生并没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这部《毘陵徐氏宗谱》。他将这部书籍认作铜活字印本,实际上只是在转述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先生的介绍。以前我虽然也曾来过两次东洋文库,但过去对于古籍版本内容的关注,只限于历史研究中利用古代典籍以及弄旧书消遣所需要的一般常识,对印刷史或版刻史研究,还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没有想到过要去核实一下相关情况。近来,因为在学校教书讲版本课的缘故,逼迫自己不得不对印刷出版史稍稍花费一些功夫,结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审视现在通行的一些说法,发觉似乎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其中铜活字本问题,最为明显,而对这部所谓铜活字印本《徐氏宗谱》,更是疑云重重。恰好近日因蒙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先生相邀到日本东京访学,并承东洋文库理事长斯波义信先生热情接待,遂得以至东洋文库,观览其宝藏,便首先想到,需要找出这部族谱和多贺秋五郎先生的著述,以一探其究竟。
根据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佐竹靖彦先生和妹尾达彦先生的介绍,知多贺秋五郎先生过去供职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部。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多贺氏的学术专长,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族谱,而不是中国古籍版本或中国古代印刷史。我所见多贺秋五郎先生关于中国族谱的研究著述,共有两部:一部题《宗譜の研究》,所出版者似乎只有其计划中的一部分,即其中的《資料篇》(整个书名可以译为《宗谱研究·资料篇》),1册,出版于1960年,由东洋文库印行;另一部书名为《中国宗譜の研究》(《中国宗谱研究》),上、下两册,出版于1981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印行。这两部书都是很有分量的学术巨著,遗憾的是多贺秋五郎先生已经故世,无从求教其当年著录《徐氏宗谱》版本的依据。不过,通观这两部著述,可知多贺氏虽然对中国族谱的印制方法有所涉及,但并没有过多留意版刻形式问题;并且从书中有关家谱版刻印刷的叙述可以看出,多贺秋五郎先生本人,对中国版刻似乎也不具备很好的鉴别能力,其所说版刻类别,恐怕只能是承用藏书单位已有的著录。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贺秋五郎先生在这两部著述的文字叙述部分中,都没有具体讲述此《毘陵徐氏宗谱》的版刻形式问题,只是在《宗譜の研究》第一部《解說》的第五节“體裁與印刷”部分当中提到(页30,页35),就其所见而言,族谱的铜活字印本,仅见于华中地区,而注释中列举的具体书籍,就是这部《徐氏宗谱》。除此之外,在《宗譜の研究》一书之第二部《日本現存宗譜目錄》里面(页129),也列有东洋文库收藏的这部《毘陵徐氏宗谱》,著录的书名系写作“徐氏宗譜”;而在印刷形式项下,著录的正是“銅活”二字,张秀民引作铜活字印本依据的正是这一项记述。后来多贺氏在《中國宗譜の研究》一书中,虽然在其它方面,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包括著录了更多世界各地收藏的族谱,但对所谓铜活字印本问题,却没有更多新的增益。
对于多贺秋五郎先生规模庞大的族谱研究来说,这部《毘陵徐氏宗谱》的印制方法,只是其中无关宏旨的一个细枝末节,他原本就无须为此一一从头探讨,援用版本鉴别既有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做法。然而,张秀民先生却是在做专门的版刻和印刷史研究,尤其是他还特别偏重对中国古活字本的研究,即使看不到原书,也不宜简单转述他人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使提出这样的主张,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不宜像他所做的那样,将这一看法视同定论,率尔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新闻出版》卷“铜活字”条,页318)。既然是在做专门的研究,对于其中所关非细的核心问题,就需要做出起码的分析与判断。这恐怕不能算是苛责于人,而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在东洋文库编纂的《東洋文庫所藏漢籍分類目錄》之《史部》第十《傳記類》“家乘之屬”江苏部分(页93),著录此《徐氏宗谱》,正是写作“清咸豐八年毘陵賜書堂銅活字印本”。不过,《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是分成经、史、子、集诸部陆续分册编纂出版的,此《史部》分册出版于1986年,大大晚于《宗譜の研究》的出版时间,因此,多贺秋五郎先生对《徐氏宗谱》的著录,不可能源出于此。这样一来,剩下来的唯一途径,似乎只有图书馆的藏书和索书卡片了。检视东洋文库的索书卡片,知此《徐氏宗谱》自是已然著录为“銅活字印”。察看索书卡片的纸张、字迹和墨色,显然已经历时很久。可以推测,多贺秋五郎先生当年将这部《毘陵徐氏宗谱》视作铜活字印本,实际上只能是在依样移写东洋文库的这一藏书底簿。
那么,东洋文库所著录的这一版刻性质,究竟是否可以信赖呢?前面已经谈过,若是不采用技术检测手段,目前辨认铜活字印本,实际上只能依赖书中的注记题识或其它有关文字记载,中国的版刻史研究者如此,日本学者也不会有更高超的眼力。下面就来逐一考察,在这部《毘陵徐氏宗谱》书中,是否存在这类文字标识。
(1)内封面。这是清代经常用来标示书籍印行方式的地方。日本版本学界习惯称内封面处为“見返”。东洋文库的索书卡片上著录有“見返『毘陵徐氏宗譜』”字样,多贺秋五郎先生在书中也原样抄录了东洋文库所著录的这一内容。今检视此《徐氏宗谱》原书,知其内封面样式,系按照大多数清代书籍惯例,分作左、中、右三栏:右署“咸丰岁次戊午校刊”,标明印制的年代为咸丰八年;中题“毘陵徐氏宗谱”,这是这部族谱的正式书名;左注“翰
墨诗辞嗣刊”,旨在说明尚有族人诗文有待后续印行。不但没有任何使用铜活字的注记,而且连“活字”都根本没有标示,乃是借用刻本中惯用的“校刊”二字,来反映族谱的印行事宜。
(2)书口。从明代起,有许多活字本就是在书口处标示其印制方法,如今人所谓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就往往在书口上印有“会通馆活字铜板印行”字样。如前所述,《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此《徐氏宗谱》,云乃“清咸丰八年毘陵赐书堂铜活字印本”,此“赐书堂”三字,即出自族谱印本版心之下部,版心上部相对位置处,则排印有“徐氏宗谱”四字,除了卷次和页码之外,书口上再别无其它文字注记,当然也绝无“铜活字”的字样。《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之“铜活字”云云,似乎也只能是依据馆内从前的卡片底册。
(3)牌记、题识、序跋。在这部《徐氏宗谱》书中,未见牌记和任何印书题识。逐一检核每一篇序跋,特别是族谱执笔者徐国华所撰跋语,以及乃师太子太保翰林院学士贾桢撰写的序文,均只字未提族谱是采用哪一种活字印制的问题。另外,在此《徐氏宗谱》卷首,印有“续修族谱记名”一项内容,开列参与族谱编纂校印的各项有关人员,其中也没有透露出一丝一毫铜活字的痕迹。
(4)正文。由于时间关系,这次无暇逐一审读,不过,一般不会在内文里说明这类印书形式问题,估计东洋文库的司理人员和多贺秋五郎先生,也不大可能花这样大的力气,来逐页查找一部族谱的印制方法。
(5)其它相关文字记载。从内容上看,这部《毘陵徐氏宗谱》,是清代江南地区一部极为普普通通的族谱,谱主徐氏也是当地实在平平常常的一个家族,人们一般没有理由对其多加理会,特地予以记述议论。所以,目前只能就有关族谱纂修主要成员的记述,适当加以考索。东洋文库以及多贺秋五郎先生,都著录这部族谱为徐隆兴、徐志瀛等修纂,但具体检读族谱,知徐隆兴虽名列卷首《续修族谱记名》“主修”者之首位,徐志瀛亦列名“编次”者之首位,但实际一手主持其事并秉笔撰述族谱的人,却是署名“监局”的徐国华(这种只挂名、不做事的情形,同古今官修书籍以及时下许多还算不上官修的名人主编书籍的“挂名主编”,道理相同)。光绪时徐氏家族复又第十次重修族谱,在这部光绪十修《毘陵徐氏宗谱》卷三十三中,收有署名“侄孙徐家华”撰写的《叔祖寿苍公传》(页1~2),文中在述及徐国华纂修九修族谱一事时,仅记云:“乙卯,捷音北闱,厥后在京,闻金陵荆棘,毘陵多恐,于咸丰六年,即归故里,尽心孝养。……因是辍馆务,静坐一室,……以己身任举事,无论难易,俱以敬出之。”也绝然没有提到用铜活字印制谱书的事情。据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卷首《续修族谱记名》,这位为徐国华作传的侄孙徐家华(按,据徐家华撰《叔祖寿苍公传》,徐国华本名寿苍,号静山,国华是其应考时使用的“榜名”,所以才会出现有若祖孙联名的现象),是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中列出姓名的两位“校对”人员之一,在其名下且附有说明云:“各支皆有人校勘,惟二人无分彼此,与局始终。”由此可知,徐家华对九修族谱的印制情况,应当了若指掌,所说特别值得注意。
接下来不妨再勉强来看看根据印本的字迹墨色,能否看出此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为铜活字印本。严格地说,这部族谱,其实并不是通篇采用同一种方式印制,而是由活字摆印和雕版刷印两种方式组合而成。所以,其内封面上所题署的“校刊”二字,也不完全是随便沿用刻本惯用的语汇来表示活字排版,而是书中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刊”制的版面。具体地讲,其绝大部分内容,是用活字摆印;另有一小部分内容,主要是以前所修谱中已有的旧序、人物传记、墓志铭文和朝廷诰赐等,乃是使用清代前期康熙至乾隆年间旧谱中所镌刻的版片,重新刷印。《毘陵徐氏宗谱》中整版刷印的这一部分,在此自可置而不论;而谱牒中新排印的这一部分版面,其字迹墨色,在我看来,则与同一时期江浙地区普通的木活字印本,没有任何区别:既看不出雕制铜质活字或许有可能出现的字形稚拙情形,也看不出金属活字印书或许有可能出现的着墨不佳迹象。相信东洋文库的司理人员和多贺秋五郎先生,也绝不可能仅用肉眼的视力,即清楚判别出它应属于铜活字,而不是木活字印本。
综上所述,以我本人疏浅的文献判读能力和非常有限的版本见识来审度观察,我认为,至少没有任何文字证据和肉眼可见的版刻特征,以资证实这部《毘陵徐氏宗谱》有可能是采用铜活字所印,甚至连极为轻微的征象也没有。
不仅如此,若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似乎还可以看到一些与此恰恰相反的迹象。
在中国古代,虽然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清楚探知,铜矿资源“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史记·货殖列传》语),分布比较普遍,但大多数矿藏,储量并不很丰富,相对于其庞大的需求量而言,一向显得比较稀缺;加之冶炼非易,又被铸成货币,用以交易,遂使得铜成为一种颇为昂贵的金属。用铜活字印书,不仅要动用大量铜材,铸字钉、刻字印还要耗费众多工时,成本之高昂,非同寻常。例如,略早于此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的福建林氏“福田书海”铜活字本印书,其事主林春祺,为刻就一套活字所耗费的白银,竟高达二十多万两。这显然不是随便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想做就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
林春祺不惜工本刻制铜活字印书,一是因为他家里有钱,二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动用这些钱。所以,不管以铜活字印书这件事,在旁人看起来有多么荒唐,只要他本人执意去做,自然也就做得到。然而,徐氏家族印制族谱的情况,却显然与此不同。
一是徐氏家族财力并不十分充裕。这一点其实本用不着多事考究,前述此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内封面上“翰墨诗辞嗣刊”的注记,已经反映出,财力在限制着这部族谱以更为完善的面目印行于世。因为将这些“翰墨诗辞”亦即家族成员的诗文以及外人撰述的有关其家族的文字,汇编成为所谓“传芳集”,与家谱一并刊布,是明代后期以来编印族谱的通行做法,而汇编这些诗文,一般并不存在编纂上的困难,能否印出,往往只是能不能筹集到相应的费用的问题。譬如,在这部家谱卷首附印的乾隆辛巳族人徐亘撰《续刊家谱序》中就曾谈到,除了当时刊印的谱书主体部分之外,“尚有名公所赠祖先诗稿数百首,欲刻无资”(页3),足以说明此九修族谱标注之“翰墨诗辞嗣刊”,其所“嗣”者,实际上正是印制的费用。东洋文库收藏的这部九修《徐氏族谱》,实际印有一部分他人“为先世所撰传赞志铭”,以及极个别一两篇“题赠序文”,但其它大量往来诗赋,特别是乾隆修谱时就已经纂辑成册的“先世自制文翰”(俱为族谱卷首《修谱凡例》语,页2),终究亦未能印出,这表明徐家确实没有足够的财力。
前述此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使用过去不同时期雕制的版片拼凑印制而成,这样一来,使得整部族谱的字体和版式,参差不一,很不像样,特别是有些部分,譬如卷首所列“历朝仕宦甲乡科贡监廪庠及异途等科目”一项内容,不过几页篇幅,却是前半使用康熙旧版重刷、后部用活字摆印,两相拼凑,尤其显得乍眼。这一点同样反映出,徐氏家族确是没有充裕的财力,来完整地排印新修的族谱。执笔撰述这部族谱的徐国华,在所撰跋语中曾明确谈到,他编纂这部族谱,值其“事垂成”之际,曾“适以岁祲中止”;逮至“戊午春,复申前议,始克蕆事”。一场天灾引起的歉收,即迫使其不得不中止族谱的编印事宜,说明这一家族显然不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徐氏若是连铜活字都轻易制作得起的富豪家族,似乎绝不应该出现上述这些情况。
另一方面,在这部九修《徐氏宗谱》中,虽然没有专门记述徐氏家族的资产状况,但透过一些相关的记载,却可以清楚看出,徐家财力不仅谈不上充裕,而且还显得颇有些窘迫。如族谱中记云:“始祖企梅公本姓徐氏,家世横林,因二亲辞世,无人抚养,自幼育于江邑之焦,因仍焦姓。自公历今,阅世有七,丁及百人,惜贫乏者多,无力建祠。所有公银二十馀两,采取些须,为每年祭祀之助。”(族谱卷首康熙丙午十四世孙徐思诚撰《徐氏家规十则》,页4。)公用族产只有区区二十多两银子的家族,显然用不起异常奢侈的铜活字。
其实,就连普通的印本,徐氏之族谱也曾因家族资材单薄,难以刊印。明朝万历年间,徐氏第十五世族人徐鲁,纂成族谱,即因财力不济,“惜乎无力刊布”(族谱卷首《毘陵徐氏祖先传赞》之《十五世澹元公传略》,页43)。下延到清代乾隆年间,当徐氏重修族谱告成之时,主其事者亦称:“百馀年就废之祠,三十载未修之谱,同时修竣,实非易事。……苦吾宗少殷实之家,捐项有限。”(族谱卷首乾隆庚戍十八世孙徐运球撰族谱《总跋》,页1。)直至这回第九次重修族谱之前,在道光年间第八次修纂族谱时,徐家更是“沦落”到“致春秋两祭”尚需“醵分以供牺牲粢盛香烛之用”的地步,即族人临时凑钱购买祭祀祖先的用品。面对如此拮据的艰难现状,其“二十世孙荀芝愀然伤之,遂将本镇历年所捐放出而几归无着之银数十两,使(族人)廷椿取讨之,廷枚登记之,榷子母以生息,几及十载。除修葺宗祠之外,将所馀之钱,置田二十亩”(族谱卷首道光九年二十世孙徐懋撰《祠田记》,页1),方始稍稍改善徐氏家族的处境。这应当就是咸丰年间重修族谱时徐家族产的基本背景,足见其绝无制作铜活字印制族谱的能力。二是族谱是整个的家族的事务,纂修和印制族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所有家族成员共同出资,徐氏应同样如此。譬如,在这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卷首印出的乾隆辛巳十七代孙徐亘所撰《续刊宗谱序》中,就曾讲到,当时是“族众共议,共襄胜举,派捐刊板”;或云系“谋诸族众,并行刊板”(页3)。由众多家族成员凑集来的钱财,花费的方式,自然也要经过家族主要成员的集体商议。乾隆年间徐氏纂修家谱时募集来的家族公款,即“凡收入须记明某年月日某人捐资捐田若干,或正用,或置产,悉有公账,各执合同察核”(族谱卷首乾隆庚戍十八世孙徐运球撰族谱《总跋》,页1);道光年间重修族谱时,也是“凡此谱所收,用以给工料之费者,其详悉登记,以俟对核,勿吝勿靡”(族谱卷首二十世孙徐廷枚撰《八修族谱记》,页1)。这便不能像福建林氏“福田书海”印书那样,因纯粹是他林春祺一个人的事情,动用的是个人资产,想怎样用便怎样用;即使饶有资材,族产万贯,也很难想像徐氏家族的众多成员,会像林某人一个人做事那样,在一瞬间统统都发此奇想,花费浩大工本,特地刻制一套铜活字,来印制这三十年才编纂一次而且也只印行最多不过一百部上下的家谱(据此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卷首《领谱字号目录》页1~6,这次编纂的家谱,诸支族人共领走九十五部)。
单纯就印刷家谱而言,普通木活字的成本,要明显低于刻本,这也是族谱通行用木活字印刷的主要原因;而铜活字的成本,则大大高于刻本。所以,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徐家人若是花费天价刻制铜字,结果竟然印出一部在所有人看来与普通木活字印本都毫无两样的谱书,岂不是要成为当地他姓人士的天大笑柄?这一点,也是我很早以前从一开始接触张秀民的说法,就很怀疑这部《毘陵徐氏宗谱》会有可能属于铜活字印本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角度看,无论如何,在当时动用巨额钱财制作铜活字来排印一部族谱,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重大事情,当事诸人和有关人士,在谈及这一族谱时,绝不应该像前面所叙述的那样,从秉笔撰稿并主持其事的徐国华,到自始至终司职校对事务的徐家华,再到特地为其门生徐国华作序的贾桢,都绝口不谈这一壮观异常的印制方式。
综上所论,不妨姑且在此妄自判断,这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绝不可能是铜活字印本,东洋文库的著录,其中必有讹误(对于图书馆来说,由于藏书繁多,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足为病)。虽然将来有条件采用技术手段鉴别,也可能完全推翻我的看法,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似乎还只能得出上面这样的结论。
正如多贺秋五郎先生在《宗譜の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清代江苏、浙江、安徽诸省的族谱,大多数都是用木活字摆印,其中江苏常州的武进,与浙江的杭州和安徽的桐城相并列,是中国各地家谱中木活字印制最为兴盛的地方(见该书第一部《解說》之“體裁與印刷”,页30),而武进正是常州府治所在的“附郭县”。在《清代的木活字》一文中,张秀民先生也曾指出,“清代活字家谱以江浙两省占压倒多数,而两省中尤以旧浙江绍兴府江苏常州府为最多”,其中“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因拥有独特的细土垫板技术而被称之为“泥盘印工”,以致还有远在四川的人,会把宗谱稿本寄到常州,雇佣这里的谱匠排印;甚至安徽省的官员,竟将省属官书局“曲水书局”特地设置在邻省江苏辖下的常州(原刊《图书馆》1962年第2、3期,见《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页225~226)。又常州武进为业师黄永年先生生长的故乡,蒙黄永年先生垂告,先生少时尚见城中多有木活字印书铺子,招揽摆印乡间文士之诗文集等项生意。徐氏家族身处这样的印刷环境,而铜活字的印制效果又并不比木活字更好,他们理所当然地会采用当地最为通行的木活字来印刷族谱,根本没有理由别出心裁,耗费巨资,专门制作铜活字来印制其谱牒。
至于当初东洋文库在著录《毘陵徐氏宗谱》时造成这一讹误的具体原因,由于历时甚久,人事屡经更叠,现在恐怕已难以追寻。我初步推测,大概存在下述两种可能。一是东洋文库与此同时尚入藏有其它家谱,馆中在初步整理著录这一批家谱时,由于排在此书前面的其它家谱,已经著录有“活字”或“活字印”、“活字本”、“木活字本”之类的版刻属性,在著录到这部《毘陵徐氏宗谱》时,司理人员便在其书名下添注有“同活字”或是“同活字印”、“同活字本”这类字样,以表示其版刻性质与前者相同;而后来进一步整理时,却疏忽误将其认作“铜活字”或是“铜活字印”、“铜活字本”,正式记入簿录。二是东洋文库在购入此书时,书店是将其定作“铜活字本”出售的,入馆后著录时便遵用书店认定的版本,未再加以考究。
这一疏误,后来被读书用书者一直承用下来,以致竟影响到版刻史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内一般叙述版刻史的概说性著述,由于不具备相应的审辨条件,不加思索地原样转述张秀民先生这一很不审慎的说法,似乎应可以理解;可是,任职于美国的钱存训先生,在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著其造纸与印刷分册《纸与印刷》一书时,也同样简单对待这一问题(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V:1 Paper and print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216.),恐怕就难以辞却粗疏之咎了。
这一偶然疏忽所造成的错误影响,事实上还远远不止于此。历史研究中错误史实判断所带来的危害,犹如投入湖陂水面的石块,它所激起的波纹,会随着距离和时间的推移,而愈推愈远,愈推愈大;显而易见,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是站得越远,受其拖累的危险性越大。譬如,清华大学的李伯重先生,近年在阐释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发展的社会意义时(见所撰《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一文,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页94~107,页146),便是遵循张秀民先生等人对版刻史研究的既有看法,举述这一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作为清代江南出版印刷业延承明代所谓“常州铜板”之先进技术而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其实,目前在版刻史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将所谓“常州铜板”认定为铜活字印本,也从来没有可靠证据,对此我另有专文论述)。李伯重先生论述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已经超越版本史或是印刷史这样狭促的“小道”,进入堂堂皇皇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范畴,对于认识清代社会,自然关系重大,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这也是中国版刻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拓展的方向。不过,假若本文所述拙见尚可聊备一说的话,像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许也可以在新的事实基础上,重新梳理并深入审视它的经济史或是社会史意义。
其实,历史学与印刷史或是古籍版本学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前者将后者用作基础工具,或是仅仅被动地诠释疏解其历史学意义,同时,还可以、而且非常需要,利用相关的历史学知识,来论证版刻史问题,二者相辅相成,需要融会贯通,交互阐发。譬如,从经济史角度讲,中国古代按照当时的技术方法,用铜活字来印书,成本过高,极不合理,所以,只能是皇家内府或极个别权贵富豪的个人行为,终究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产业。因而,对它的评价,除了单纯的技术探索意义之外,丝毫也不值得夸耀和赞誉。这部《徐氏宗谱》的印制方式,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印刷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实际上却是判断中国以铜活字为代表的金属活字印刷在社会上流行程度最重要、而且也几乎是唯一的标志,一旦否定了它的存在,随之自然就会引出一个与传统说法截然不同的重大结论。我将另行撰文,论述相关问题。
对于渐行渐远的历史,今天我们究竟怎样来进行研究,才会更具有深刻的意义,时下东西学人的念头,是愈出愈新,愈出愈奇。人各有所好,学亦各有其用,学者自可各遵所闻,各行其是,而且学术研究也只有拓宽视野,多从新的角度加以思索,才能不断有所发现,抱残守缺,治学绝不会有什么出路。不过,学术研究最本质的真谛,首先是研究者要有足够强烈的探索兴趣和欲望。有些领域过去很少有人研究,往往是由于它缺乏足够的复杂性、学术难度和更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从而也就未能吸引研究者驻足,并不都是因为前人鼠目寸光,竟会为一株不知名的小草而忽略了苍茫林海。遵循这样的思路来审视我们所面临的研究课题,传统的领域和问题,正因为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很可能还需要不断深入探索,并不是研究得多了,研究得久了,就已经穷尽其事,了无新意可陈;甚至很多习以为常的通行结论,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予以颠覆。因此,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更不能忽略与旧有研究的交互衔接,这些传统研究领域在相关研究中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决定了立足其上的各项新的研究,都不宜简单另起炉灶。事实上,新的研究视角,常常可以为解决传统的疑难问题,提供至关重要的切入点,二者正应互为补充,不宜偏废其中一端。
在探索寻求新的路径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应该首先努力站稳脚跟。在这纷纷纭纭变化多端的学术风潮当中,或许也能够找出万变不离其宗的共同立足基点。中国的历史学人,近年比较普遍地尊崇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成就,以我涉学之浅,一直还无法读懂先生的高妙见解,特别是先生所揭示的中古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脉络;不过登高自卑,致远由迩,我很喜欢陈寅恪先生讲过的一句非常浅显的基本治学方法,这就是“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陈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语)。研究版本目录这类形而下下的问题,更要强调从第一手史料的审辨做起,更要讲究无徵不信,更要注重首先证之以平平常常的人情事理。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审辨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的版刻问题,使我对此复深有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