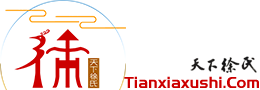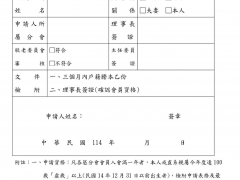说起金门之战,了解情况的人无不嘘唏不已。刘亚洲在他的《金门战役检讨》一文中如此描述这一仗:“九千余人渡海进攻金门,在岛上苦战三昼夜,因后援不继,全军覆灭,无一生还。”时至今日,我们才知道。“无一生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广饶县大码头镇央上村徐钦林就是生还者之一。在金门之战中,他既没被俘也没战死,他的经历传奇得令人难以置信。前不久,在他的农家小院里,徐钦林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当记者问起金门战斗时,老人不住地叹气,看得出来,几十年的时间不足以疗去那锥心之痛。
说起我在金门的经历,很多人都不相信,现在想想,连我自已都说不清楚当时是靠什么信念挺过来的。1946年12月,我们村74位青年一块入伍,都被分到渤海军区11团(后来的251团)。唯独大字不识一个的我当了炊事兵,心里那个烦:我来部队是扛枪打仗的,又不是来做饭的。于是,抽空我就去重机枪排,和他们一起练扫射,后来,就连团长刘天祥都知道3营炊事班长重机枪打得好,在打上海时,我团机枪排长负伤,刘团长临时任命我为重机枪排副排长。如果不是那次机会,就没有后来我在金门的曲折经历,因为当时大家普遍认为打金门是“小菜一碟”,一顿饭的工夫就解决了,炊事班就没过去。
记得那天是1949年10月24日,我所在的28军84师251团3营是从小嶝岛过去的。大约25日凌晨两三点钟船靠岸。部队一上岸,即遭遇国民党青年军。刚开始,战斗打得很顺利,敌人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部队的士气也很高涨。可是仗再往前打,我就发觉情况不对劲。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敌人三四十辆坦克往前冲,后来才知道这时敌人的兵力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料。到了中午,敌人8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每20架一组,炮弹像雨点一样不停地落在阵地上,硝烟弥漫。阵地已经被炸了个遍。部队也被打乱了。这时我们这个18人的机枪班只剩下两三个人,我一边在敌人七八辆坦克中穿梭,一边命令副班长往西南方向撤。撤出二里多地时,我感觉小腿发凉,一看小腿被打穿了。血顺着打穿的洞口正往外流。当时连长在身边。我把机枪递给他,“我的腿打断了,枪给你。”
59年前的今天,我正在金门水草中呆着,样子很狼狈。光着脚,穿着单裤单褂,晚上扒块老百姓的地瓜吃,水都喝不上。当时敌人的搜索队还没来,我身边还有几个重伤员,有的伤口已经化脓,蛆一堆一堆的,惨不忍睹。我挣扎着爬到烈士遗体中寻找急救包。给重伤员包扎伤口。唉。后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地牺牲,大约四五天后,我来到附近一户老百姓家里。家里没有人,我四处看了一下。这户人家的大门上有鸽楼。可以藏身。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后续部队很快就能打过来,我要挺住。等待部队的救援。挨到天黑,我悄悄来到海边,眺望远方有没有船只,可是,望穿泪眼,连只小船的影子也没有。白天在鸽楼上,我也不敢睡觉。侧耳听着有没有猛烈的炮火声,我们的后续部队是不是和敌人接上火。就这样日伏夜出过了三四天,一直没动静,看来部队打过来的可能性不大了。怎么办?泅渡?不可能,腿部受伤,又没有充足的准备,弄不好会葬身大海。自杀?战场上没战死,自已结束自已的生命,太丢人现眼,死也要和敌人同归于尽。正在想办法脱身时,户主发现了我。因为三四天中,我每天下来偷点他家煮熟的地瓜吃,地瓜无缘无故地少了,我也就暴露了,很快来了一个班的国民党兵。
按照常规,我也就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可事情偏偏巧在我当时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说起这身军装,还有一段故事:在解放大嶝岛时,我军俘虏了一批国民党士兵。这批士兵没换军装就补充到我们队伍里,名曰“阶级兄弟新战士”。在我的教育下,一个新战士认识到当国民党兵的耻辱,坚决要求更换服装,还说:“穿黄狗皮打国民党,打死是为党国阵亡还是解放军烈士?”但当时又没有新军装发给他,作为班长,我只好把自己的军装换给他。就这样,我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坐上前往金门岛的船只,谁知就这一换为我换来了一条命。这伙国民党兵厉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灵机一动:“你看不出来吗?我是25军(国民党的部队)的,负伤走不了了》”他们看我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也没细问,就说:“你往城里爬吧。爬到医院去养伤。”说完就走了。我这才知道国民党军队是不管伤员的。
后来,我在水草中滚爬了十几天,又是靠着这身军装,来到了金门城里国民党118师师部医院。在医院里呆着,伤是慢慢治愈,可我心情更加焦急。一般情况下,伤员治愈后,立即就地当兵,”守金门保台湾“。扛国民党的枪不说,一旦被送到台湾,想回大陆就更不可能了。于是,伤好了我也不丢拐仗,整天叫痛叫痒,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四个月,医院的医生,护士,伤员都认识我,见面还打招呼。其中有个国民党的中校,带个勤务兵在医院养病。国民党江南吃败仗时,他和住在长沙的老婆失散,不愿意去台湾,于是留在金门任金防补给主任兼辎重营长,负责闽浙沿海敌岛补给。他是河北人,喜欢吃葱油饼,北方口味的菜,而我以前是炊事班长,又是山东人,这些活自然不在话下。他的勤务员做不好时,我就替他做。他吃得高兴,时间长了对我说:“跟我干吧,当我的私人挑夫兼伙夫,不会亏待你的,”我自有打算:跟着他,留在金门,不去台湾,又能在闽浙沿海来往,回归大陆的机会更多,于是满口答应。
1950年2月份,我随中校坐运输舰来到舟山群岛,到后来才发现这儿的守敌不同金门,松松散散,挖工事装样子,当官的也不过问,而且我们是坐着空的运输舰来的,我一分析,心中窃喜:看来敌人准备撤退,这一仗我军定能胜,部队很快就打过来,我回大陆也指日可待。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随他走遍了舟山群岛的仓库,码头,把敌人驻军分布,岗哨位置摸得一清二楚。一天早上,大陆方向海滩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猛烈。中校坐不住了,趁他刚点着一支烟的工夫,装糊涂地问他:“演习吗?”他摇摇头,情绪有点烦燥,“你去看看,快去快回。”我拿了把刀,赶快往山上跑,先观察一下地形,发现西北方向有座大山,离脚下二里路,是一个躲避的好去处。这时天助我也,正好有一阵大雾。于是,我迎着雾,没命地朝山上跑,一口气跑到山沟里。坐下喘口气。害怕中校派人追来,我选择一个隐蔽的水草丛里躲着,还找来一堆石头,手头一直拿着那把刀。我当时想:国民党兵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两个。就这样在水里泡了三天,所幸国民党兵也没来。第三天,听到附近的村子里鬼哭狼嚎,我判断是国民党撤完了。我一阵高兴,想马上站起来,可身体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连动都动不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出山沟,顺着枪声寻找部队。首先遇上的是7兵团24军。一看到他们,我的眼泪刷就下来了:经历半年时间,我终于又回到部队。接下来,我提供的详细情报对战斗很有帮助,很快舟山群岛解放,我也跟着他们回到了杭州,后又从杭州转到10兵团司令部。
到了10兵团司令部,我在政治处学习了三个月。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被审查,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该同志脱离党组织六个月,按照规定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处理。这留党察看一察就是30多年,直到1986年中央落实有关政策才恢复党籍。这中间也有人劝我重新入党,可我没有,因为我坚信总有一天组织上会查明情况,给我恢复党籍。1951年,我被调到龙岩军分区连城县大队,1952年复员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