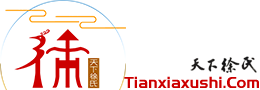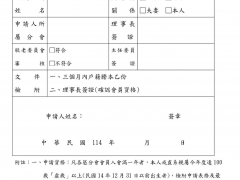探访山东济南的古村落,我们希望发掘它们身上独特的存在光泽,希望窥见历史和现实交汇处,一个个时代切片。当外人用新鲜的眼光打量这些古村落时,这里的人也用新鲜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外来人。

写不开的家谱正如不知未来的古村命运记者邵猛摄

立在古村里的地排车,不知是哪家搬离时留下的。 江丹摄
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古村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学者说,它是民间文化生态的博物馆,是民族根性文化的物质载体。但事实上,古村落的消亡却已触目惊心:在去年济南召开的“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上,冯骥才曾告诉本报记者,古村落现在处于最危急的状态,“根据湖南大学对17个省113个县的村落调查,2004年,总共有9700个有传统历史的村落,但是到了2010年,只剩下4700个,每天损失1.6个。”
正是这种“危急状态”,促使我们出发。
古村落的传说固然传奇,古村落的美景纵然动人,但浮于表面的白描并非我们的初衷,深入内里的探索才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相信,在现代文明的大潮中,最古朴的文明生态,一定会经受最惊心动魄的撕扯、挣扎,与突围。
探访济南的古村落,我们希望发掘它们身上独特的存在光泽,希望窥见历史和现实交汇处,一个个时代切片。
古村落不是“桃花源”
7月17日,记者驱车前往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的方峪和岚峪,探访这两个时常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古村。当外面的人涌进来欣赏它们的古朴时,那里的人却正急于摆脱眼前的落后,踏寻远方的城市。
老石屋和新房子
汽车驶过新方峪,却开不进老方峪。前者是近些年村里在山下的平地上统一搬迁新建的村落,年轻人都搬了过来,水泥混凝土的房子与其他地方并无二样。后者则是那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村落,时常在影视剧的镜头里出现,石板房石板路,零零落落住着四五十户老人家。
79岁的方庆祥就住在这样一栋老石板房里,前后3个院子,有300年历史,住过方家10代人。
老屋墙上有两幅大照片,一幅是老伴儿的遗像,黑白的。照片里的老太太安详宁静,年轻的时候,她在这老屋里纺线织布,洗衣做饭,和她的大娘婶子一起,照应着一大家子的衣食。家里的男人下地回家,她们端上热饭,等男人们吃完了,这些女人再上桌。
另一幅照片,则是方庆祥新近刚拍的,彩色的。照片背景像是海南的椰林沙滩,方庆祥穿着衬衣,还有一件黑外套。在方庆祥看来,这次拍照经历神奇极了。
老人忍不住要跟记者分享这份神奇,“去年两个南方人来村里拍的,就在大队支部门口。”方庆祥说,“当时我就穿了一件衬衣,拍出来我还多了一件黑色的褂子,他们用电脑给我弄上的。10分钟就弄好了,才25块钱。”
其实,不过就是简单的电脑PS,但方庆祥不知道那是什么,除了神奇只剩下神奇。方庆祥记得,10年前老伴去世时,急需一张遗像,孩子拿着那种一寸的小照片去扩印得跑到镇上,还花了五六十块钱。
得知记者想再给自己拍张照片,方庆祥从晾衣绳上拽下一件汗衫,执意套在原本光着的膀子上。他站到前院的大门口,任由记者拍摄。住在道路另一侧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看见记者举着相机,关上门躲到屋里去了。裹着小脚的这位老太太,害怕记者的相机摄了她的魂魄。
方庆祥家门前的这条路,近4米宽,曾经是这个村落里最为繁华的地带,有名望的大院、当铺都曾立于一侧。如今,这里冷冷清清,只有几户独居的老人。
年轻人不愿住在这里。方庆祥的儿子一家便搬到了山下的新房子里,那里的房子更高更宽敞,交通也更加方便。
而在附近的岚峪,山上的老屋大多已经坍塌,断壁残垣,青草野蛮生长。村里的人搬到山下,或重新择地而建,或就地翻盖,建起了红砖水泥的新房子。69岁的王孝晨就住在这样的新房子里,夏天日头毒,晒透了墙体,屋里热。更多的时候,他喜欢蹲在屋角的阴凉地里凉快凉快。如果是老房子那种半米厚的石墙,指定晒不透,屋里就很凉快。但他依然喜欢现在的新房子。“现在都盖这样的,这是潮流。”王孝晨说。
当外人用新鲜的眼光打量这些古村落时,这里的人也用新鲜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外来人。
“进屋坐坐,我给你们烧水喝”
因为媒体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方峪,尤其是周末,这里时常会出现一队一队的学生,他们来这里写生。偶尔,这里也会出现学者和剧组,他们来这里研究这个古村落的标本,或者拍摄他们心中古朴的镜头。镇上计划着在这里发展旅游,把古村落的历史和生态资源转化成产业经济。
在这些外面的人眼里,这里就是桃花源,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牙齿掉得七零八落的老头儿老太太坐在门前的石板上晒着太阳,或者推着那种足以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小木车下地干活儿,车轮碾轧过门前凹凸不平的石板路,吱吱呀呀,仿佛是历史的回响。
方庆祥乐得和这些外面来古村瞧新鲜的都市人打交道。如果有人在他门前经过,他会跟他们聊两句,“进屋坐坐,我给你们烧水喝”。曾经,他还帮助一个影视剧组找群众演员,拍摄一天,每人得到了60元的报酬。
但是,方庆祥的孩子却不赞同老人的做法,“不认识的人尽量不要往家里领。”慢慢地,方庆祥也有戒备,他有自己一套判断“好人”和“坏人”的方法。比如说,碰上有人问他家里有没有老家具什么的,他一定会关上门不搭理。
老村里的人对外人并无多大防备。记者在岚峪采访时,本来只有王孝晨一人,路过的人看到有外人坐在那里聊天,也停住坐下,打量着记者,然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他们说,村子里的青壮年大多去外面打工了,农忙的时候才回来,这里是山区,还是靠天吃饭,今年的麦子减产了,每亩只有600斤,村西头的集市快起来了,该去买菜做饭了。
讲不清的家谱,“写不开了”
与方峪完整的古村落片区不同,岚峪的现代气息更为明显。从村口走进岚峪村,看到的是房龄不超过十余年的砖瓦屋舍,并没有想象中古村落该有的历史厚重感。在村委委员赵玉亭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深藏于村中的张家古宅。
古宅墙壁由方正的石块砌成,正房为二层的“张家楼”,墙体厚达80厘米。61岁的张应福正躺在一张小床上午休。
对于这座古宅的历史,身为张家后人的张应福并没有讲出很多,“父辈没有说多少。”他了解的张家历史颇为简单:几百年前,先祖兄弟两人从北京通州地区来到山东,一位留在这里,一位南行至泰安,从此落叶生根,繁衍后代。能建起这样的古宅,张应福自忖,先辈一定是大户人家,“普通人家吃饱饭可能都有困难,哪里建得起这样的二层石楼?”
在追忆先祖家产丰足时,张应福从一只木箱中找出自家的家谱。如同古宅,张应福同样说不清家谱历经多少年岁,“到我这一辈是16代,你可以算算。”张应福伸开折叠的家谱,“始祖,二世祖……直到我这一辈,写在最后一折。再往后,写不开了。”
张应福有一儿三女,儿子在外已经10多年,女儿也都已经出嫁。习惯于生活在老村中,张应福多次拒绝儿女接他进城的想法,“我守在家里,看门,种几亩地,自力更生,好赖老在这里,几十年的老窝住得习惯,城里既不方便又不肃静。”“写不开”的家谱如何往下续?几十年后,百年古宅是否还有张家后代居住?生死不离故土的张应福或许并没有清晰的答案。那些从古村走出去的年轻人,更没有答案。他们离开古村,在远方的城市打工,再回到古村时,竟然陡生一种陌生感。他们已经离不开城市,便也无法真正回归这里的故土。“在城里,他们是外乡人,但在这里,他们也好像成了外乡人。”赵玉亭说。古村的历史再久,根脉再深,也抵挡不了岁月时光中现代文明的磨打,终究会有断壁荒草,终究会有无根的人。(邵猛 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