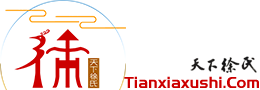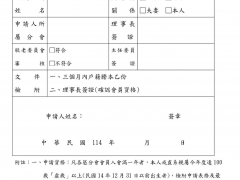一、观前街前
观前街过去是乌镇比较热闹的一条石板路,现在仍是新乌镇的一个中心,来此之前,我对它的两个关键词:修真观戏台和茅盾故居,并不陌生。
这一记既说到中市,那就先移步到常丰街的两个新设的景点:汇源当铺和访卢阁去转一转。
常丰街上一座乌黑气派的房子,当街一个墨黑的“當”字,如一条恶狗挡道,旧时百姓走到这个地步,也算是霉头触尽了。即使今天抱着游戏的心态走进当铺,也总会有一种压抑,自然,触摸着近两米高的柜台,或许有些兴奋和神秘,但一部典当的历史,不会像你我今天反背着双手,大摇大摆着走进去那么轻松自在。
汇源典当是徐氏九世孙徐焕藻开设的,徐氏素有令名,四乡农民,如急需用钱,一只石臼也是可以入当的。当然,石臼不用抬到当铺里来,说一声也就可以了。当年,徐家的当铺,柜台上并无栏杆遮挡,柜台也要比如今修复的低许多,说到底,这与徐东号的牌子有关。但,当铺的围墙厚且高,这是毋庸置疑的。厚且高的围墙,到底也挡不住太湖强盗的长枪,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大批湖匪自西北栅入口,在转船湾排队鸣枪,向全镇四栅同时实施抢劫,汇源典当首当其冲。
当铺入北,不几步,就是传说茶圣陆羽访救命恩人卢仝的茶馆。水乡的茶馆,原本多如蚁穴,完全可以撇开瞎七搭八的传说。这家名叫访卢阁的茶馆,也算名声在外。踏着楼梯上去,却未见一位茶客。时在正午,正是午茶时分,一问价钱,三十元一壶,贵了。这个地方,我小时候其实没少来,旁边原是一爿新华书店,我翻书,大人喝茶,两不误。当年的红茶,不过几分一壶吧。这才是老百姓吃得起的茶。而茶馆店的气氛,就是靠这伙短衣帮吃出来的。
过应家桥,往东,即看到修真观戏台,观始建于北宋咸平元年(998),屡毁,屡建,好在国人重名分不重实物,体现永恒的不是建筑物而是一个观名。多少朝代更迭,原初的实物早灰飞烟灭,但观名留传至今。观前的戏台最后一次修缮是民国八年(1919),还算得上乌镇的一个老古董。细心的游客当看到台前左边石柱上隐约有这样的文字,“宪奉禁演淫戏台下勿须堆积”,右边“同治十一年五月青镇里民重建”。由此看来,乌镇人民早在一八七二年同治皇帝治下,已经有扫黄打非的高度责任感了,所谓“堆积”,轧闹猛也。修真观戏台古时是轧闹猛的地方,现在仍是,锣鼓一响,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观前街17号,这四开间两进深的两层木结构老楼房,是茅盾祖上的旧居,1896年,一代文学大师诞生在这里。楼上有茅公一生事迹陈列,天井里有他手植的天竹一棵,一抹青翠点缀在黑白的氛围里。比较而言,茅盾仍是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最好传人。
与故居毗邻的,是立志书院。这座1991年按原样恢复的小小书院,是乌镇文风鼎盛的鲜活见证,它的历史说来话长,最初由邑绅严辰于同治四年(1865)创建,拈取乡贤张杨园先生的治学格言“大凡为学先须立志”之“立志”二字,作为书院名称。小天井里的桂花树,隐含“蟾宫折桂”之意。与书院仅隔一条观前街的文昌阁里,祀奉着孔圣人和天上的文曲星,那是当年读书人的一块圣地,因与茅盾家贴隔壁,少年茅盾没少来阁楼上白相。
观前街,因街前有修真观,故名,俗呼南街,因西起应家桥北堍,也叫应家巷,有一个时期,它叫“解放北路”。董志上说,那个地方有卖刀削面的,当年“京浙称美”。我缓步徐行,但见旅游商铺林立,有一家干脆叫上了“林家铺子”,卖蓝印花布,卖姑嫂饼……店家脸上,个个热气腾腾。
观前街东至横街为止,其长不过一百九十米,这一段是乌镇的华彩段落,这一段,目下排门气派,石板路修洁、整齐,瓦楞沟挺括,似乎连滴下来的檐头水,也是崭新壁陡的,充满了吆喝的热情。
二、庸园劫灰
大概民国三十年(1941)吧,寓居上海的作家孔另境已经十多年没回老家乌镇了,他突然接获来自魂牵梦萦的老家的不祥消息,占领乌镇的日军焚烧古镇,两天一夜的时间,“把一条青镇精华的东街完全焚毁。”其中自然包括孔家素称乌镇园林精华的庸园。孔家其时虽已破落,但旧宅尚好,劫难发生时,东街大部分难民逃集于庸园的几间破屋中避祸,一些难民还就此暂居下来。孔家老宅已无人料理,孔另境担心故园中的花木家具,以及断椽梁木,怕是要作难民用炊的燃料了,当来人问他怎么办的时候,孔家的这位长房长孙双手一摊,说了一句很无奈的话:随它去吧,算了!
孔另境名令俊,是茅盾夫人孔德沚之弟,1904年出生在青镇,他是在俗称孔家花园的庸园里出生并长大的。另境幼时,甚得曾祖父庆增公的喜爱。
庸园是孔庆增的得意之作,也是他一生的魂魄所系。孔庆增,字云峰,性喜风雅,以酿造业起家。孔家原在观堂桥东,旧有乌镇著名的孔家花园,可惜毁于咸丰庚申之乱,卢学溥《乌青镇志》云孔庆增于光绪初年“就财神湾宅后辟治园亭,引泉成池,叠石为山”。《孔氏东家外史》亦云:“(庆增)八九年高,童颜貌若,喜种花木,创造庸园。”孔庆增去世于光绪三年四月,他算是那个时代镇子上有眼光的人物。
但孔家看中财神湾,似应更早,孔庆增一下子购买了几十亩地,唯财力所限,先筑住宅三进,造了十多间屋子作酿酒的场所,屋子后面,多出的十来亩地,暂时莳花种菜。其后,孔氏渐至发达,孔家花园也逐渐地成就了规模。孔另境说,大约孔庆增五十岁上,这位小镇的成功人士特地去苏州聘请工匠,来经营他一生的梦想。他派人去太湖一带运了几船太湖石来,建筑假山,历时一年,费了数千银子,庸园最终建成。此说与镇志及外史记载有出入,想来此时所筑,不过是庸园的雏形吧。
关于庸园,孔另境《庸园劫灰录》一文,有详细记载。兹录一段描述稍长的文字如次:“全园分为三部分,成了一个凸字的形象,进门的一座长楼,是放置他的古玩字画的,接着是一座平厅,这是第一部分;从厅后转出,为第二部分,傍建钟楼一座,楼下接连一座小假山,山下为鱼池,内蓄金鱼数千尾,其大者超过半尺,池边满植瓜子黄杨,高与屋齐,池之傍为一小亭。亭后连以曲折之小屋,屋底有秘门如书橱,以手扶之,橱即开动,越此秘门,即入第三部分,放眼一望,即觉眼界大展,忽现另一种景象。倘谓第二部分以精巧胜,则第三部分颇可以说得上‘雄伟’两字了。在从秘门进来的地方也是一座亭子,亭旁为一座竹园,走出亭子为一石子砌成的甬道,甬道的尽端乃现一座大石山,高可三楼,分三道可上,山下有洞,中置石几椅等,山上连接一楼,甚为壮大,约有五六开间,上置匾额曰‘月圆人寿之楼’。楼内布置似客厅,楼之东西面墙上不开窗而凿一大圆洞,下置小梯,登梯望洞外,可见全镇景色,此为全园最高处,亦为本镇最高之楼,远在镇尾,亦可望见此巍然之大楼。楼下之旁有一个鱼池,范围较前者为大,也蓄有金鱼无数,池中并置有荷花台数个……第三部分之后,尚有菜圃甚大……”
孔庆增有文人的雅致,却不以文人自居,他认可自己的“生意人”身份,取名“庸园”,大约是自贬之意,无非怕别人讥笑他冒充风雅,但这个生意人,却做成了乌镇园林史上最后一件大作品。
乌镇的园林,自唐裴休在黄家板桥西筑“长廊蔽日”的“裴休府”开始,宋有沈平宅第东皋园、秦申王桧园等十六处;元有员外颜旒宅一处;明有王英、王济父子之横山堂,李乐之拳勺园等十七处,清有徽商严大烈所建之宜园、严辰翰林第等十四处;民国尚有张氏适园等五处。特别是南栅河西的适园,密植嘉木,四周环以碧草,“上有高台,登台四瞩,则寿圣塔矗于东,田野村舍互于西,而吴兴诸山亦远在烟云缥缈之间。”通过民国二十三年春剡溪人陈醉的笔记,我们尚可领略其中的韵致。庸园的建造,自然是乌镇绵延千年之园冶的余续,也可以说是乌镇造园艺术的最后一次高峰。
因为有孔另境细致的描绘,后人大抵还能觉出庸园不凡的气势。我在最近出版的孔另境的一本散文中,还看到一张孔家花园(庸园)的示意图,是一位陆姓老人根据当年亲眼所见回忆绘制的。凭借着这一张示意图,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我来到东栅财神湾西边的原孔家花园,拉开矮门,是一间极普通的民居,八十五岁的女主人许兆年接待了我。许兆年十八岁嫁到孔家,在此已经生活了六十多年,许兆年的丈夫是“祥”字辈,论辈分,她比茅盾、孔另境都要大一辈分,说起来,茅盾是她的侄女婿。和老人聊了一会儿天,我即起身,随人走入内室。打开后门,抬头所见,是一个天井,里面植着两棵桃树,天井的北面,是一片竹林,竹林尽处是一道围墙,越过围墙,还是一片竹林,总共大约有十来亩地的样子;往北,另有一道围墙,第二道围墙外,才是一片白地。当年的老房子,如今只剩下边上的围墙,但幽深曲折冗长的规格,却是镇上别处的房子中极为罕见的。老宅中,有一棵高大的广玉兰,两枝金桂,几枝枇杷,甚是可爱。只是,当年庆增公亲植的几百枝高过屋脊的黄杨树,我一枝也没有见到。老宅前半爿住人,收拾得整齐修洁;后半爿,是一片废园,枯黄的竹叶,堆得厚厚的,踏上去,快淹没我的脚板了。
当年的庸园,应该包括现在孔家住屋东边贴邻的孙家厅。许兆年说,孙家厅原是郑家的房子,郑家是孔家外婆家,后来,郑家败落,卖与孙家。孙家原籍绍兴,光绪末年,孙秀林挑着一副笸箩,带着一家五口,步行来乌镇,吃苦耐劳,加上精明睿智,孙秀林开始发家,买下孔家花园的东半爿,从此,孔家花园、孔家厅的一爿,一变而为孙家花园、孙家厅。
孙家花园是文学家木心先生出生的地方。木心,1927年生,木心是笔名,原名仰中,字璞,先生五岁时,父亲孙德润(孙秀林之子)去世。1948年,木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毕业,1982年去国,左手画画,右手为文,木心的文章,得二陈(陈丹青、陈村)绍介,近年渐为国人所知。
隔着一堵墙,我听到了孙家花园里传出的电锯的声音,还飘过来一阵现代的油漆气味。
兜一个圈,从公路旁的东门口进入孙家花园,青砖砌就的小洋房赫然在目,转入里面,厅堂俨然,当然是新修的,刨花满地,建筑的杂物堆成了小山。出得厅堂,来到一个“正式”的花园,假山堆耸,池水是怪异的绿,弯曲的水池边,挂下去、挂下去的藤蔓,肆意地疯长着,像是要触及一个旧梦。
“有一年,木心回来看自家的老房子,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我说:‘你是孙仰中!’”
木心很惊讶,“你怎么认识我?”
“我与你阿姐同学。”
许兆年回忆那一次意外的相见。她还记得木心母亲和木心小时候的情况:“木心母亲是大块头,木心小时候文气,长,瘦。”
1997年冬,游历了大半个世界后,木心先生悄悄来到乌镇,只为了瞥一眼老家,东栅北栅,所见“运河两岸大抵是明清遗迹,房屋倾颓零落,形同墓道废墟,可是都还住着人。”现在,东栅经过整修,财神湾也阔大气派得多了,但除了阿拉阿拉的一拨拨上海人,乌镇原住民却愈发的少了。东栅成了一个景观的区域,细民歌哭生聚的细节,睿智如木心先生,该到哪里去找寻呢?
三、东栅之东
东栅是乌镇最先开发的一个所在。重新整理以后的东栅,大排门,石板路,深宅,大院,果然展现了当年的幽深曲折。东栅的开发,目前止迄于财神湾,财神湾当年即是“市集较胜”的地方。财神湾以外,一个更其广大的东栅,已经被大多数人忽略。
由财神湾而外,低头走过公路桥堍,我径直向东栅之东走去。
路已经是水泥路,两边的房子断断续续,已经无法连片成一定的规模。突然,我心头一喜,看到了一爿老式的剃头店,店前的街沿石,焦黑的影子依稀可见,石面上,有烧灼的痕迹,石皮迸裂的伤痕——这是当年的东洋人作下的孽。
东栅之东有徐东号,乌镇俗语:徐东号的牌子,张同盛的银子。说到徐东号,乌镇东栅的最东面,不是三里塘,而是大上海了。
近代以来,上海开埠,对江南小镇的吸引力可谓巨大,一些豪门巨富纷纷移居沪上,谋求发展,徐氏并不例外,相反,徐氏家族早在道光后,比别家更早一步踏进了上海滩。
上海的某处,有乌镇路和以乌镇命名的桥,这是托了徐东号老板徐冠南的福。当年,上海英租界工务局开拓苏州河一带市容时,寓居宁波路乾记衙的徐冠南捐银赠地,才得以让乌镇之名镌刻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史上。
现在的东大街111号,是徐东号的旧址。街北,一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泥房子,原来是一个烟厂,现在似乎仍是一个什么厂。但当年徐东号雄视乌镇的楠木厅,已经了无痕迹(据说1990年以前,楠木厅架子笔挺,破壁残垣,还在)。倒是街南宽阔的河埠头,长长的条石,可以想见当年徐东号的气派。
徐氏祖籍上虞,雍正年间始迁乌镇,徐氏在乌镇,从开设米行、香饼行发家,道光后,开始向上海发展,至九世徐焕藻、徐焕漠兄弟,又在乌镇开设云锦绸布庄、汇源典当等,徐氏“富遂甲一乡而轻财好施……凡地方善举,皆力任不辞”。至徐冠南,已历十世,凡两百年。徐冠南主要的实业已在沪上,业银行业和房地产业,民初,徐冠南的资财,已达七百五十万银元,成为大上海首屈一指的富户。
徐冠南乐善好施,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徐家在上海发达之后,将乌镇的田产低价或无偿过户给佃户,徐东号的牌子,是几代人努力创制的结果。再比如,徐氏尽力提携故乡亲友,单是保荐俊彦之士,“有一定知名度者达八十余人。”1916年,沈雁冰(茅盾)北大预科毕业,进商务印书馆,是徐氏提携的结果。茅盾后来创作《子夜》,不少素材即来自徐氏在沪上创制的富户“星期六聚会”,这是徐冠南的儿子欣木先生亲口所说。
但,就是这样一位善举连连的民族资本家,民国十三年被绑票,耗银二十八万,不久又因替人作保受牵连,赔垫三十万银元。徐氏的凋敝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民国二十六年十月,日军入侵乌镇,东栅徐家厅遭日军火焚,当铺被日机炸为平地,一家人避难途中,屋漏偏遭连夜雨,又被湖匪洗劫,受战火的牵连,徐氏实业纷纷倒闭,民国二十九年,徐冠南病逝于沪上,徐氏从此一蹶不振。“徐东号的牌子”,从此长存乌镇人的记忆之中。
透过乌镇东栅徐东号的一张小小牌子,世人也可见出中国早先一代民族资本家盛衰兴亡的历史。还是孔夫子的那句老话: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区区一个家族,哪里逃得出这个铁定的规律?
(邹汉明)